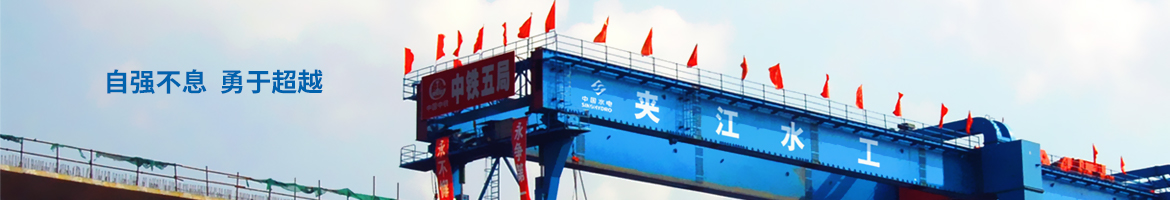黄土的暖痕 | |
| |
黄土高原的冬,是天神遗落的旧陶胚。沟壑是它未及抚平的指痕,风在梁峁间打磨了千万年,只把苍茫磨得更薄、更透。山是脱了釉的,树是烧过了火的,连天空都像蒙着层坯布。羊群移动时,仿佛是大地偶然渗出的几点奶沫。唯一能缝补这破碎山河的,是家家烟囱里抽出的灰白棉线——还有爷爷扬起的鞭梢,在小卖部墙根下老人们的闲话里,脆生生地劈开凝固的光阴。 我的母亲,就立在苍黄天地这枚粗陶碗的碗底。 她几乎不识字。可她的记忆是部活的黄土志。货架上每一包盐的价格,木格里每一种兽药的名称,都长在她掌心交错的纹路里。那些弯弯曲曲的笔画,于她不是横竖撇捺,而是羊群的寒热、耕牛的咳喘、骡马胃里的胀气。她将粉末与药片包进黄纸时的神情,像在为土地把脉,指尖触到的是整个高原怦然的脉搏。 她给予的,总是多过交易本身。八十年代末,她递给独坐门槛老妪的一瓶甜水,塞进脏兮兮小手里的两颗糖,不是施舍,是她从自己日子里匀出的、一小块一小块温润的糖色。她替堂兄凑齐的学费,是点亮另一孔窑洞的灯油。她的名字,便这样被许多苍老或稚嫩的唇齿含着、暖着,在村落的风里传成一段柔软的线,织进了黄土的经纬。 而我们姐弟,是她最倾心的作品。 她的肩,是托我们远行的塬。都市的楼影再高,根基是她铺就的土;弟弟们脚下的路再宽,源头是她踩实的坡。如今,我们已在各自的新地图上扎根,她却退回到那两间旧铺子里,退成电话里永不疲倦的叮咛,退成年节时灶火前一个愈显瘦小的背影。 她最盛大的节日,是团圆。当子孙的喧嚷塞满四合院,当我们的筷子伸向她烹调的整个故土——那盘浓缩了阳光的腌缸肉,那碗沉淀了秋实的臊子面——她的笑容才完全绽开。那是一种被需要的、踏实的丰足,是她为自己索求的全部报偿。 母亲啊,我的西北母亲。 您是以自身为渡船,将我们从此岸的荒凉,摆渡到彼岸丰饶的人。您不书写传奇,您自身便是从黄土里长出的、最韧性的传奇。您用一生,在我灵魂的版图上,烙下永不冷却的暖痕。 愿那炊烟为您升起得更久,更直。 愿您佝偻的肩,终于能卸下岁月,只托住属于自己的、那片轻暖的晴空。(责任编辑 蒲玉凤) | |
| 【打印】 【关闭】 |
| 浏览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