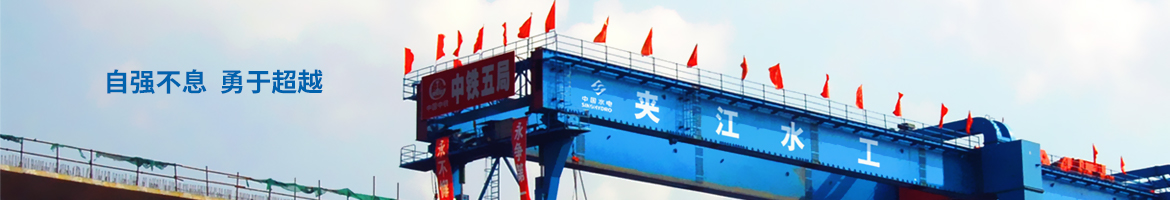锁在抽屉里的爱 | |
| |
这是我在广西钦州遭遇的、第一个名义上的冬天。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漫过一片片棕榈叶,扑在脸上是黏腻的、温凉的。我站在制造场边缘,眼前是即将发运的巨型风电塔筒,钢铁巨物在亚热带的天光下反射着冷硬的银辉。它们静默地躺着,像史前巨兽的骨骼。空气里弥漫着金属打磨的辛辣气味与海风盐粒的涩味:这是属于我第六个工作年的、具体而微的现实。 而手机屏幕上那个无声的数字,“十月一日,寒衣节”,却像一枚从遥远北方射来的、精准的楔子,骤然钉入这潮湿燠热的现实,撬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口子。寒意并非来自钦州的空气,而是从记忆的深处,从那片名为会宁的黄土高原上,呼啸而来。 我的外婆,就在那片黄土之下,长眠了整整五年。 时间过得沉默而迅疾。从初入夹江水工的青涩,到如今能独当一面地在钦州这陌生的海岸线上监造这些庞然大物,六年时光被压缩成一份份图纸、一次次验收报告和一张张差旅票据。生活被这些坚硬的、可量化的东西填充,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这种钢铁般的秩序。可“寒衣节”这三个字,却能让这一切瞬间瓦解。它像一把无形的钥匙,试图去开启一把早已锈蚀在北方的、小小的黄铜锁。 那锁,挂在家乡老屋、那具红漆斑驳的五斗橱最上面的抽屉上。在我们三个外孙的童年里,那方寸之地,是世间最神秘的宝藏窟。外婆开锁的动作,总是一套缓慢而郑重的仪式。她从斜襟衫最里层的口袋,摸出用红绳系着的钥匙串,就着屋里昏暗的光线,眯起眼,找到最小的那一把。钥匙探入锁孔,“咔哒”一声,在我们屏息凝神的期待中,这声响宛如天籁。 抽屉拉开,一股复杂得难以形容的气味便弥漫开来:陈旧木头的沉香、防蛀樟脑丸的辛冽,以及一丝被小心藏匿起来的、甜美的油脂与糖分的气息。那是独属于外婆的、关于宠爱的密码。她的手伸进去,摸索一阵,再攥着手拿出来。我们三颗小脑袋便迫不及待地凑上去守着。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叠成温暖的漩涡,手掌缓缓摊开,有时候是几颗印着红绿条纹的水果糖,玻璃纸在昏暗中也能折射出梦幻的光;有时候是一小包用粗糙草纸包着的动物饼干,小兔子和小熊的形状憨拙得让人不忍下口。 “来来来,一人一个,不许抢。”她软糯的乡音,是这馈赠仪式最后的、温柔的。那糖果或饼干落入我们掌心时,总带着她手心的温度,一种干燥的、被黄土高原的风沙浸润过的温暖。我们便欢呼着跑到院子里,蹲在墙根下,用最慢的速度,极其珍惜地舔舐或啃咬那份被“藏”起来的甜蜜。 那时,我们只顾着吞咽着甜味,何曾懂得去品味这“藏”字背后,外婆那近乎本能的、深沉的爱意?她把生活中所有稍微金贵、稍微美好的物事,都像鸟儿筑巢般,一点一滴地收集、珍藏起来,然后用一把锁,郑重地封存。那抽屉,是她用自己全部的细心与节俭,为我们构筑的一个抵御世间所有贫瘠的、温暖的童话。我们,是她唯一且永远的读者。 在夹江水工上班后的第一年听到外婆病重消息时,我刚独立跟着第一个项目。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压抑着哭腔,背景音里仿佛有北方旷野的风声。我请了假,坐上北上的列车,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青翠欲滴,渐次褪色为北方的灰黄萧索。我见到她时,她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安静地躺在土炕上,像一片被风干的落叶。我握住她的手,那曾经能变出无数惊喜的手,此刻冰凉而僵硬,只是无力地承接着我的颤抖。她浑浊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似乎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只化作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她终究没能越过那个冬天。送葬时,纸钱在会宁干冷的风中打着旋,像灰色的雪。我望着那条通向坟茔的、被冻得坚硬的路,心里空了一大块。我知道,那个会为我们藏起甜蜜的人,走了;那个童话王国,随着它的缔造者,一同陷落了。 如今,我在这片几乎感觉不到四季流转的南国土地上,终日与钢铁打交道。我的世界,是由精确到毫米的尺寸、严格的探伤标准和冰冷的焊接工艺构成的。我站在庞大的塔筒节段里,听着卷板机的轰鸣,监督着焊缝的成型。这坚硬的一切,与那把小小的黄铜锁,与锁背后那张慈祥的、布满皱纹的脸,仿佛隔着无法逾越的时空。 寒衣节了。按照北方的旧俗,该为地下的亲人焚化纸做的寒衣,让他们抵御另一个世界的风霜。会宁的北风,此刻想必已如锋利的铡刀,能割裂天地了吧。外婆,您一生都在用您的方式,为我们“藏”起温暖,挡住尘世的风寒,如今,我们该去哪一片旷野,点燃那件能为您御寒的衣裳? 海风从塔筒的端口灌进来,带着永不消散的潮气。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那件印着公司名称的工装外套,这致密的人造纤维,却隔绝不了那从心底一阵阵泛起的、北方的寒意。外婆,您把所有的好,所有的甜,都小心翼翼地藏进了时光的深处,却把那把开启记忆的钥匙,永远地留给了我。我在这片终年常绿的土地上,在钢铁的丛林里,徒劳地寻找着一个可以投递思念的地址。 那一声遥远的、来自童年的“咔哒”轻响,总在不经意间,回荡在钦州这黏湿的、称不上冬天的空气里,清晰得令人心颤。(责任编辑 蒲玉凤) | |
| 【打印】 【关闭】 |
| 浏览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