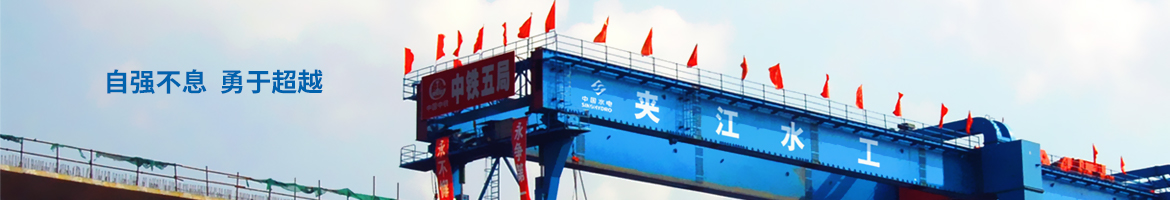时间的锻件 | |
| |
今天,又是立冬了。 窗外的厂区,笼罩在一片铅灰色的天幕下。高大的厂房默然矗立,纵横的塔筒泛着金属特有的冰冷光泽。棕榈树的阔叶在潮湿的海风里懒懒摇曳,空气温润,丝毫没有冬日的凛冽。时光的流逝,在平日里被琐碎的事务填满,不易察觉;唯有当“年”这个巨大的刻度再度浮现时,才会蓦然惊醒,回头望去,来路上已立起了五座沉默的冬碑,而自己,已经走向了第六座。 我的第一个立冬,是在总装车间的喧嚣与油腻中度过的。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实习生,满脑子是书本上的公式定理,面对眼前的钢铁的森林,却显得手足无措。巨大的天车吊着数十吨重的构件,在面前隆隆滑过,那沉重的阴影,带着一种物理规则特有的权威,压得人几乎屏住呼吸。老师傅们用大锤敲击钢铁的声音,清脆、笃定,仿佛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他们可以与之对话的老友。而我,只能跟在后面,递工具,看图纸,用棉布一遍遍擦去设备上永远擦不尽的油污。那个冬天,空气里弥漫着铁锈的味道,我的世界,是由钻孔、螺栓、公差尺寸构成的。立冬对于我,不过是节气表上一个模糊的名词。那时的我,无法想象,这片钢铁的丛林,将会成为我安身立命的土地。 后来,我成了融合项目的工点负责人。角色变了,视角也随之拔高。我不再只盯着自己手头的那一方天地,开始学着协调、沟通,学着为运转负责。压力是无声的,却比车间的噪音更让人焦灼。也正是在这种焦灼里,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项目的工点。当图纸上的线条,最终变成一座庞然、精密、闪烁着新漆光芒的实体时,我绕着它的顶部走了无数圈。那种创造的喜悦,是沉甸甸的,它不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轻松,而是一种目睹“无”中生“有”的、近乎神圣的感动。我伸出手,触摸那冰凉而光滑的表面,仿佛能感受到它在我的手指下,孕育着即将轰鸣而起的生命。 转变,发生在我来到德阳分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新能源事业部德阳生产基地参与制作塔贝拉拦污栅、古都闸门……这些名字,至今念起来,唇齿间还带着大江大河的水汽与远方车间的焊火。那些构件是如此巨大,当它们静静地卧在制造平台上时,人站在旁边,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如同仰望史前巨兽。然而,正是这无数个“渺小”的我们,用汗水与智慧,将它们一一唤醒,赋予它们力量,让它们去往千里之外,去驯服滔滔江河。那段日子,立冬的意味淡了,季节的变换,更多地被项目的节点所替代。我们追逐的不是春夏秋冬,而是到料、焊接、大组、发运的循环。 再后来的远行,是职业生涯里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从与钢铁巨兽的搏斗,转向了与风对话。参与制造全球海拔最高的八宿风电,是一项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些洁白的塔节,将要矗立在雪域高原,去承接那来自天际的最纯净、也最狂野的力量。我时常想象,当巨大的塔筒撑起的叶片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始旋转,搅动流云,它收割的已不仅是电力,更像是一种对苍穹的叩问与应答。从沉稳厚重的水电,到轻盈灵动、直指云霄的风电,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工业血脉的转型。我们制造的物件,不再仅仅是扎根于大地,约束水流;它们也开始拥抱天空,捕捉无形。 如今,我成了事业部采购负责人。我的战场,从轰鸣的车间转移到了无声的报表、纵横交错的供应链网络和瞬息万变的市场风浪里。我可能不再直接触碰那些钢铁,但我触摸着它们的“前身”,它们的价格、它们的渠道、它们抵达我们生产线的那条看不见的轨迹。这是一种全新的“锻造”。我锻造的不再是实体,而是关系、是流程、是成本与质量之间那根绷得最紧的弦。立冬之于此刻的我,似乎又多了一层意味。它像是一个结算的节点,提醒我去盘点,去规划,为来年整个事业部采购的运转,备足“冬藏”的给养。 而此刻,在钦州,这个三年前曾听闻、后又因故沉寂的马王三期风电项目,终于复工。这像极了时间开的一个玩笑,又像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轮回。当年那个在传闻中的名字,如今成了我电脑旁堆积如山的图纸与报告。监造它与处理采购事宜并行,我仿佛同时站在了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一手触摸着一段被重启的历史,一手为远方的新能源事业输送着给养。 这个在南国海风里到来的立冬,因此有了一层复杂的滋味,让我更深刻地体味到“收藏”与“积淀”的意义。那些中断的,会连接;那些沉睡的,会苏醒。就像这马王三期,三年的等待,并未让它消亡,反而在更合适的时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六年,六个立冬。我的足迹从总装车间到新能源事业部,从水电到风电,从制造到采购。场景在变,角色在变,但内核似乎未变。我始终围绕着“制造”这个词,它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辛劳,也是荣光。 立冬,是万物收纳锋芒,积蓄力量的时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将六年的汗水与荣光,挫折与成长,一并收敛起来,沉淀为生命的“冬藏”。这藏,不是终结,是为了下一个春天,更磅礴的迸发。 今天,立冬。第六个冬天,开始了。整理好电脑边的文件,关于马王三期的,关于风电塔筒的。回到电脑屏幕上,待处理的采购相关工作正静静等待着。这个冬天,依旧很忙。(责任编辑 蒲玉凤) | |
| 【打印】 【关闭】 |
| 浏览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