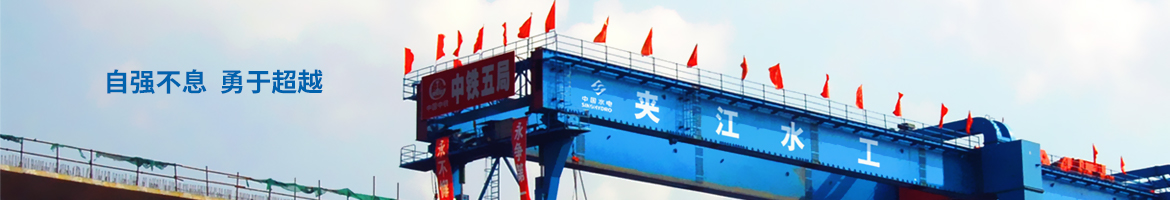黄土炕上的旧时光 | |
| |
这炕,是黄土高原的魂,是家家户户的根。记忆里,我家的炕就盘在靠窗的那头,用的是上好的胡墼(用模具做的土坯),泥是掺了麦草的黄土,厚厚地抹上去,结实得像一块烙铁。炕面铺着那张印着小红花的油布,早已被岁月磨得光滑而温润,边角有些卷起,露出底下熏得焦黄的苇席。我总爱把脸贴在那油布上,一股子阳光晒过的、混着泥土与烟火的气息,便幽幽地钻进鼻腔里来。那是一种笃实的、使人安心的味道。 炕洞里的光景,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小时候天还未亮透,母亲便窸窸窣窣地起身,抱一捆晒得焦干的荞麦杆,又寻些深秋树林扫来的落叶、草皮,混合着驴粪或者羊粪,小心地填进那方黑的洞口里去。划一根火柴,“嗤”的一声,一团橘红的光晕便在黑暗中蓦地绽放,旋即响起那噼噼啪啪、欢快而又谦逊的燃烧声。那青烟,便带着新柴的润气与陈灰的枯香,从烟囱里袅袅地升上去,融进黄土高原那铅灰色的、广漠的晨空里。这烟,是村庄的呼吸,一日不停,生命便一日不息。 炕的热,是一种慢吞吞的、往里渗透的热。它不像城里暖气的燥,也不似火炉子的烈。它是从身下的泥土里,一丝一丝,匀匀地透上来,熨着你的肌肤,暖着你的筋骨,直把那股子妥帖的暖意,送到你的心窝窝里去。冬日的长夜,窗外是北风卷着雪粒,打得电线呼呼地响。我们一家人,便都窝在这热炕上。父亲靠着被垛,一页一页的翻阅着那本焦黄的兽医书,噗呲噗呲的声音,像一曲催眠的歌谣;母亲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缝补着永远也缝不完的衣物;我与弟弟们,则在炕桌玩着法宝,争抢着一把炒得喷香的豆子。那时的话,是零零碎碎的,有一搭没一搭的,火炉子上水壶的雾气和豆子的焦香,在这暖融融的土炕上浮着,酿成一坛叫做“家”的醇酒。 如今,我在这千里之外的水泥森林里,冬日守着嘶嘶作响的空调,脚下踩着冰冷的地板。却总觉得那热是不熟悉的,是停在皮肤上的,怎么也暖不到记忆的深处去。我忽然明白了,我所贪恋的,哪里仅仅是炕的那一点温度呢?我贪恋的,是那被烟火气笼罩着的、完整的家的形态;是那在漫漫长夜里,亲人之间无言的陪伴;是那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最朴素的安稳与从容。 前些日子母亲在电话里说,如今村里也没几户人家烧炕了,年轻人都用上了电热炕,又干净,又省事。我握着手机,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晓得,那从炕洞里升起的、带着灰草香的青烟,终将在这片高原上越来越稀薄,直至消散。那一方土炕所承载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体温,更是一整个农业时代的、温存的背影。它正在无可挽回地,沉入历史的暮色里去。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流光溢彩,是一片虚假的、没有温度的白昼。我闭上眼,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仍是那个光着脚丫在炕上乱跑的孩童,外婆在灶间拉着风箱,火光在她慈祥的、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那炕,还是温热的,那股子混着泥土与烟火的气息,还浓浓地包裹着我。 这黄土高原上的土炕,于我,于无数如我一般的游子,早已不是一方胡墼。它是一整个沉甸甸的、暖着心肺的故乡。只是这故乡,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在梦里,在记忆深处,反复地、反复地,去触摸她那正在渐渐冷却的、最后的温柔。(责任编辑 蒲玉凤) | |
| 【打印】 【关闭】 |
| 浏览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