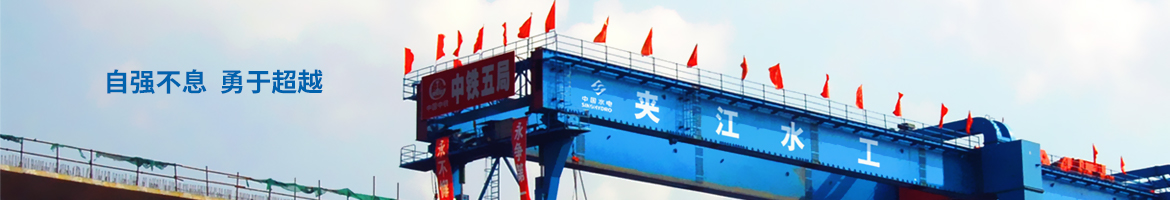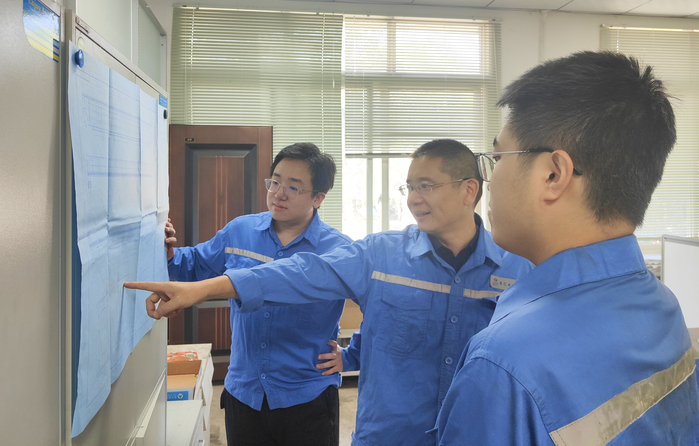【走过60年】钢铁丛林里的师徒情 | |
| |
这三四年的日子像上紧了发条,慌慌张张地往前赶。从最初工作的手足无措,到现在能沉下心梳理琐事,我渐渐悟透了“学做平凡事”——这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在日常琐碎里磨出踏实底气,在反复实践中沉淀从容心境。这份理解,是被身边的师父们悄然打磨出来的。 晨光中的第一课 清晨,当太阳初起,夹江水工夹江基地生产技术部办公室,一张门机的A0总图的四个角被磁石稳稳地固定在铁皮柜的空白处。夏师父——一位身材敦实、面容黝黑、眼神锐利如尺的老师傅——伸出他那指节粗大、布满新旧划痕与焊疤的黝黑手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在图纸上沉稳而有力地游走。所到之处,图纸的难点、要点犹如庖丁解牛般一一展现出来。那根手指,仿佛带着某种与钢铁对话的本能,精准地丈量着图纸与现实之间的毫厘。 这是新下达的门架上部生产图纸,技术组所有人正围到一起,对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有的问题进行探讨。 “门机通常就这些关键点要控制。小李,你负责这个项目,到时候一定要跟铆工交代清楚,每一个尺寸都是筋骨,马虎不得,平时多追踪进度和质量。”夏师父收起图纸,递给我,语重心长,每个字都像沉甸甸的铆钉,敲打在我的心上。他额头的皱纹在专注时显得更深,那是经年累月与精度较量的刻痕。 我接过图纸,把刚记好的要点放在上面,下决心要整好这个门架。 夕阳熔金,将车间染上一层温暖的橘红,工人们已经下班了。夏师父领着技术组一行人戴着安全帽走了进来,停在一座拼了一半、骨架峥嵘的门架前,他微微仰头,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探伤仪,一寸寸扫过冰冷的钢梁,那专注的姿态,仿佛在聆听钢铁的呼吸。 夏师父从腰间皮套里抽出那把磨得锃亮的卷尺,动作精准而利落,一段段确认起拱值是否在允许值范围内。量到主梁中心,他眉头微蹙,蹲下身又反复确认了两遍,粗糙的手指仔细摩挲着测量点。他直起身,面朝大伙,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起拱值虽然都在允许范围内,可是实际来讲,主梁中心2米范围内起拱值差值应该大一点,这对于铆工放样和产品实际使用是有帮助的,差之毫厘,未来可能就是千里之患。小李,这是你负责的产品,下次给起拱值数据在这方面要注意。”我用力点了点头,那一刻,我不仅记下了数据,更刻下了师父眼中那份对“刚刚好”的永不满足,那是对“完美”近乎苛刻的追求。我郑重地将要点记在本子上,仿佛记下的不是数字,而是关于“精益求精”的无声誓言。 突如其来的考试 眼前这座弧门足有十几米高,钢铁的巨臂在车间顶棚下伸展,远比在图纸上冰冷的数据更有冲击力,一种工业造物的磅礴之美扑面而来。我在弧台面前站了很久,不断地端详着这座弧门,合理美观的钢制结构和构思巧妙的功能设计,冰冷的钢铁在此刻仿佛拥有了生命和智慧,我似乎能看到磅礴汹涌的江流正在被这个智慧结晶的集合体缓缓地、有力地驯服、截断。 “小李,我考考你啊,为什么斜支臂弧门的支臂要向内偏转角度?”郑师父的声音突然响起,带着他特有的、仿佛总在思考什么的沉稳语调。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郑师父,一位身形清瘦、鼻梁上架着厚厚眼镜、口袋里永远揣着笔记本和计算尺的老师傅,已悄然站在我的身后。他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和探究的兴致。 郑师父的这个问题太过抽象,如果手里面没有负责过至少十几个斜支臂弧门是万万想不出来的。我果断摇了摇头,脸上有些发烫。郑师父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嘲讽,只有对知识探索的纯粹热忱,给我讲了一通他对于角度内翻的理解,我依旧如听天书一般,不禁也有些为自己的愚笨感到羞愧。 “想不通是对的!”郑师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掌瘦削却很有力,“琢磨透一个‘为什么’,比干十个活都值钱。我是老师傅尚且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通,如果你听一两遍就懂了,那你也太厉害了。”他的宽慰让我心头一暖。他引我走到侧面,随手捡起地上的粉笔头,熟练地在旁边的钢板上画出简洁有力的示意图,指着支臂端板处对我详细地讲解其中的奥妙:“你看,正是这斜支臂的‘斜’,暗藏玄机。如果没有角度内翻这个‘巧劲儿’,支臂腹板与端板之间就不能完全贴合,就像关节错位,受力不均,隐患就埋下了。这可不是图纸上随便画画的,是无数实践和计算得出的‘最优解’。”他讲述时眼中跳动着智慧的火花,那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痴迷探索。原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设计角度,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匠人的深思与实践,是力学与工艺的完美共舞。师父的讲解,不仅解开了我的疑惑,更在我心中点燃了一盏灯:技术工作,不能只知其然,更要穷究其所以然。思考的深度,决定了匠心的纯度。 李科(左)向郑师傅(中)请教技术问题 放样台前的顿悟 从图纸到拼装钢结构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放样下料。通过放样,复杂难懂的图纸转变为一块块尺寸形状详实的板材,最后由铆工拼装成钢结构;通过标注坡口形式和位置,为板材连接预制好焊接区域,最后由焊工烧焊成一个整体。这如同为钢铁赋予生命的初始密码,一笔一划都关乎最终的筋骨与血脉。 所以,放样最考察的就是读图能力。每一个刚来到技术组的人最先接受的考验就是能否准确和完整地完成一套图纸的放样,这是从“纸上谈兵”到“沙场点兵”的关键一跃。 我刚来的时候读图没问题,可是总是在下料收缩量、焊缝切角和拼装预留间隙上出问题,给铆工师傅增加了很多返工量。看着师傅们对着我标注不清的料单皱眉,甚至需要重新划线切割,那种愧疚感像针扎一样。所以后面我放样总是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怕这里错,那里漏,下笔时总有些畏首畏尾,图纸上的线条仿佛都带着审视的目光。 “莫要怕!哪个师父的成长路上没摔过几个跟头?肩膀不压担子,腰杆子就挺不直!”邓师父嗓门洪亮,性格爽朗,谢师父则更内敛些,但两人脸上总带着宽厚的笑容,笑着宽慰我,给我讲述他们年轻时出的那些啼笑皆非的错误,那些如今看来是教训、当时却是煎熬的经历。最后,谢师父指着车间里忙碌的铆工师傅们,语重心长地说:“放样下料,光盯着图纸上的线不行。你得跳出来,把自己‘钉’到铆工台上去想。钢板上了台架,怎么固定最稳当?焊枪怎么走最顺手?拼装时怎么对位最省力?你得替下一道工序的兄弟把‘路’铺顺了。怎么干活方便、高效、不出错,你就怎么放样。心里装着干活的人,手里的笔才有准星。” 我尝试这样转换视角,仿佛瞬间穿上了铆工沾满铁屑的工装,感受着钢板的重量和焊枪的热度。一张图放样哪里需要留量和切角,哪里需要标注得格外清晰,竟然成了我迫切需要解决、且充满挑战乐趣的问题。“换位”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珍贵的职业品格:懂得体谅,方能协作;心怀他人,方能成就。这视角的转换,让我放下的不仅是心理包袱,更是技术员与操作者之间那道无形的墙。 前路漫漫,山高水长。我愿继续做一颗沉默而扎实的螺丝钉,在图纸的方寸间精耕细作,在钢铁的丛林里淬炼锋芒,在焊花的洗礼下打磨自己的价值。而我的技术笔记,还在沙沙作响,不仅记录着新的数据、新的领悟,更记录着那些师父们用一生践行的信条:在平凡中追求卓越,于细微处铸就永恒。他们身上那份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凡处见真章的力量,将是我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灯塔。(责任编辑 蒲玉凤) 平陆运河项目业主验收弧门 | |
| 【打印】 【关闭】 |
| 浏览次数: |